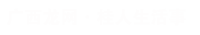彭凯平|互联网摸鱼大赏( 三 )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企业主觉得「打工的不如以前不好管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起源于工业机器化生产时期的企业的管理策略主要有两种,「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直接控制是指企业通过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设计让技术工作从工人群体剥离,并集中于管理层,这就让机器制造业的大批工人沦为去技术化的体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劳动者逐渐成为「在指令下重复劳动的新型机器」;责任自治认为技术不可能完全从劳动中剥离,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权或者说自主性。
但现代企业并没有因此完全进化,他们经常会设置一种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比如人们认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战的程序员群体,由于编程工作的创造性他们本该在劳动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但企业通过一系列生产规则、标准和微观劳动流程的设计,让这群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者的工作也变得单一乏味。
学者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型劳动者」,但其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而当这些涉及OKR、KPI等绩效考核的目标被分配到劳动者头上时,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知识民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耻感」,这种「耻感」加剧了他们的加班。
但这种加班不是自发主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意」,是被迫的过程。学者布洛维认为,在责任自治中,企业擅长运用一系列规则、标准和流程干预,让劳动者全身心投入这场「赶工游戏」,从未忽略了雇佣关系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质。换言之,看上去是劳动者自发在加班,但实际上还是管理策略在发挥作用。
坦白讲,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群体是佼佼者,中国90%的IT程序员还是在小型公司(100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上班。所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识劳动者并非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知识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他们之所以自称IT民工,计算机码农或者金融扫地僧,这些称呼背后都有身份建构的不适感。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农民可能是远离精英阶层、权利无法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身处底层的IT从业者来说,这种身份建构是自身工作状况和社会状态的重要切面。
而那些发起摸鱼小组或者说亲身实践的摸鱼娃们,很多可能也并非「没有上进心的躺平选手」,也不是「没有物质生活压力的小康之家」,他们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诉求被压抑忽视太久后,共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共情群组。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参考文献:
1.梁萌《996 加班工作制:互联网公司管理控制变迁研究》,科学与社会,2019.3
2.吴玲竹、何亮《网络新词“摸鱼”的语义分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1
3.孙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全球传媒学刊,2018.4
4.钱叶芳、徐顺铁《996类工作制与休息权立法——资本与法律的博弈》,浙江学刊,2019.4
5.大卫·格雷伯《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Simon & Schuster出版,2018.5
【 彭凯平|互联网摸鱼大赏】
- 腾讯云|海晨股份(300873.SZ)拟携腾讯云、数势科技打造供应链领域垂直互联网SaaS服务平台
- 网络红包|互联网@2022,是停滞还是重塑?
- 红包|80亿互联网红包等着你来瓜分!快来薅羊毛
- 任正非|互联网巨头“不务正业”,官媒点名,网友:多学学任正非
- 创业|新手创业小白如何在互联网上快速获得流量提高转化率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 互联网时代|全球6G专利情况公开,中国申请数领先全球,美日再次屈居二三位
- 工业互联网|等不来新《开端》,“优爱腾”十年为何还学不会赚钱?
- 蒂姆·库克|小米智慧产业园区整体交付,助力我区“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建设!
- 小米科技|360伤人事件后续:互联网公司不要再碰金融了
- 工业互联网|85%诈骗通过互联网 专家称全链路反诈才能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