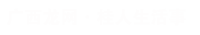“真的是一门很美的语言!”袁甜甜说 , 直到今天 , 她和学生用手语交谈 , 有时候还会愣神 , 觉得他们“身上有光” 。 而亲眼看过王建源、乌力杰打手语的人 , 就会承认袁甜甜的感受并不夸张 。
王建源生在青岛一个聋人家庭 , 父母都是听障人士 。 2018年考进聋人工学院网络工程专业之前 , 他一路都在聋校接受教育 。
小时候 , 父亲就像其他家长教孩子说话一样 , 带着王建源认认真真地练习手语 。 父亲并不认为那是一门“特殊”的语言 , “他觉得普通话能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 手语同样能够大开大合、诙谐幽默 。 ”父母对手语的坦然态度 , 影响了王建源 。 他从不避讳在公开场合使用手语 , 也从不隐藏自己的聋人身份 。 在他看来 , 手语就是手语 , 不是某种“残疾的外显” 。 聋人可以用它表达内心的想法 , 而健听人 , 只要掌握了这门语言 , 同样可以用它来交流——手语和其他任何语言一样 , 是破除障碍、沟通彼此的工具 , 它可以是桥梁、是纽带 , 唯独不该是障碍本身 。
乌力杰是来自青海的蒙古族小伙 , “家在茶卡盐湖边上”——除了精通手语 , 他也可以用口语交流 , 只是声音有些沙哑低沉 。
比起同年入学的王建源 , 乌力杰的求学经历要更复杂些 。 小学阶段 , 他靠助听器和读唇的本领 , 与健听孩子一道读过三年普校 , “三年都是全班第一” 。 那段经历锻炼了他的适应性和口语表达能力 。 后来 , 他离开青海 , 在武汉第二聋校完成高中学业 , 通过单考单招来到天津理工大学 。 这样的成绩在家族同辈的孩子中“笑傲群雄” , 更让他坚信“聋人也不比谁差” 。 他一度直接把“Deaf-无音”用作自己的微信昵称——在英文中 , Deaf就有聋人的意思 。
无论是学专业课、推广手语还是做科研 , 这个古铜色皮肤的蒙古族青年有股“一马当先”的闯劲儿 , “海伦·凯勒能做到的事情 ,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技术之难
王建源和乌力杰是受袁甜甜邀请加入项目团队的 。 2019年 , 他俩才上大二 , 就被委以重任 , 负责收集手语语料 , 撰写符合自然手语语法、语序的句子 。 手语是一门视觉性语言 , 基于这一特点 , “撰写”的过程不是通过手写或打字输入 , 而是以录制视频的方式完成的——王建源、乌力杰以及团队中其他听障生的重要工作之一 , 就是对着摄像头反复打手语 。
为什么是他们?
因为手语实时翻译技术之难 , 恰恰源于手语之美:
独立的语法体系 , 意味着团队研发出的系统 , 除了要将单个手语词汇的意思识别出来 , 还得把手语语序转化为健听人习惯的汉语语序 , 把手语的“火灭”调整成“灭火” , 才算完成翻译;独特的空间感 , 意味着高度相似的手语动作 , 在不同的环境中 , 可能有不同的译法 , 计算机要学着区分“屋外的太阳 , 屋里的灯”;丰富的表达方式 , 意味着手语识别不像语音识别那样 , 只需收集“声音”这一种“学习资料” , 要把人工智能训练成一个合格的手语翻译 , 得把手势、表情、大肢体动作 , 通通从视频转化为数据 , 再“教”给计算机 。 所以 , 能充分理解、展示手语之美的听障生 , 是最适合给人工智能当“老师”的人 。
王建源和乌力杰“教机器”学手语的本事 , 来自“教人” 。
尽管年纪轻 , 他们的手语教学经验却可谓丰富 。 刚上大一 , 他们就发现 , 对手语心存偏见的人不在少数 。 不止健听人 , 即使在听障生内部 , 也有很多同学 , 因为从小就受“打手语就是承认自己有残疾”“要像‘正常人’一样讲话”等观点影响 , 对手语怀有抵触情绪 。
- 儿童教育|首个播放量破 100 亿的 YouTube 视频诞生,竟然是儿歌
- 东南亚|MIUI13深度使用报告,这还是我认识的MIUI吗?网友评价很真实
- 酷睿处理器|旗舰背后故事!1亿像素超清摄影+骁龙778G,你认为它适合什么人
- 降噪|苹果确认iPhone 13移除了电话降噪功能 此前机型均配有
- CPU|红米k50系列基本确认,整体安排跟k40差不多,双4nm芯片确实香
- 寒假来了!这节“交通安全”课,请认真看
- Flash弹窗广告卷土重来?3步定位,5步彻底关闭!手把手教程奉上
- 36氪|启中教育:如何实现店铺爆发式增长
- vivo|xplay6,音质好确实好,不过vivo我只认同这一部手机
- 欧菲光|郭台铭还没认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