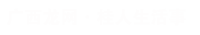华裔数学家张益唐知乎讲述:“这一辈子就是做数学的命”( 二 )
很多人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 , 觉得我花了这么多年研究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 , 有没有想过放弃 ,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 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 。
关于Landau-Siegel猜想 , 我没有想过放弃 , 因为这些年我的整个思考也是断断续续的 。 2007年我发过一篇关于Landau-Siegel的论文 , 其实当时是有可能继续做下去的 , 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个情况 , 就是孪生素数的问题一下变得热门了 , 所以2010年到2013年去做孪生素数去了 , 就做出来一个7000万的结果 。 后来想想 , 觉得Landau-Siegel还得做 , 所以就又回到这个问题上 。 我一般是几个问题同时在想 , 一段时间注重这个 , 一段时间注重那个 , Landau-Siegel实际上上世纪末我就开始想了 , 我喜欢几个问题一起想 , 有一个问题初步想出来了 , 其他那些就接着想 , 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
前几天论文公开后 , 我给北大做了一场远程讲座 。 我在北大时的导师潘承彪评价:今天听了益唐讲的想法很清楚 , 这是一个重要的筛法新思想 , 有很大发展潜力 , 可实现起来很难 。
我当即回复:听了潘老师的肯定 , 比听一万个人的赞扬更有价值 。
今天 , 我又和知乎上一个关注我论文的小伙子交流 , 了解到他在伦敦读大一 , 学数学 。 我觉得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 因为他大一已经能够学到我在研究生时候学的课程 , 说明他进步很快 , 付出了很多 , 确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小伙子 。 希望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 不要把前人的东西看成至高无上的 。 这个东西别人这么做的我能不能换一种做法 , 或者我能不能突破它?不断自我提问 , 不断自我尝试 , 走出新的路子来 ,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前程是非常远大的 。
关于我的未来 , 这些数学问题我是不会丢掉的 。 我觉得我大概这一辈子就是做数学的命了 , 我不做数学都不知道干什么 。 别人谈过退休的问题 , 我说如果我真的离开数学了 , 我确实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
平时在家里 , 我夫人总是觉得我一个人不太说话 , 吃完饭自己在房间里一待 , 耳机一挂自己听音乐 , 玩自己的 。 她怕我这样慢慢会神经 , 还开玩笑说 , 我老了要是神经了 , 她可受罪了 , 还得给我推轮椅 。 所以她每天把菜切好让我回家以后学炒菜 , 不管炒成什么样也要炒 。 周末有时候也找几个做数学的同事来家里坐坐 , 喝酒聊天 , 但他们说我聊着聊着眼光不对 , 走神了 。 夫人经常批评我这样不礼貌 , 说我这样将来就没有朋友了 。
我夫人觉得我浪漫的时候不多 , 就连去维也纳听音乐会都要跑到维也纳大学 , 去找哥德尔的雕像 ,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 直到碰到一个刚下班的教授 , 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哥德尔的雕像才走 。 但是我很感谢她带我来听音乐会 , 因为我喜欢听交响乐 , 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师我都喜欢 , 首先是贝多芬 , 特别爱听他的第六交响曲 。
另外我还特别喜欢勃拉姆斯 , 其他的像柴可夫斯基 , 还有肖邦的钢琴曲我也特别喜欢 , 尤其是他的作品53号 , 降A大调波罗乃兹 。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那时候的校园歌曲 , 苏小明就是我那时候的“偶像” 。 我同学说我当年在北大宿舍里 , 谁提苏小明不好还跟人翻脸 。 前一段我和夫人去普林斯顿的时候 , 住在北大校友吴刚的家里 , 他家有卡拉OK , 我们还放苏小明的歌在那儿唱 , 可能跑调了 , 因为他们都笑我 。
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 , 其中最欣赏杜甫的诗 。 比如“剑外忽传收蓟北 , 初闻涕泪满衣裳” 。 还有“却看妻子愁何在 , 漫卷诗书喜欲狂 。 白日放歌须纵酒 , 青春作伴好还乡” 。 杜甫有他自己的奔放 , “即从巴峡穿巫峡 , 便下襄阳向洛阳” 。 百读不厌 , 怎么品这个味道都觉得特别好 。 杜甫的诗太多了 , “风急天高猿啸哀 , 渚清沙白鸟飞回 。 无边落木萧萧下 , 不尽长江滚滚来” 。 还有下面两句我也特别喜欢 , “万里悲秋常作客 , 百年多病独登台” 。 对仗对得非常好 , 而且很自然 , 流传了一千多年 , 让后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品它的味道 。
- 丘成桐成立不用高考的清华求真书院,只为培养数学家
- 丑|华裔女孩因独特拍照角度丑成网红:双下巴瞩目
- 在美华裔科学家命运“重大转变”?
- 伊隆·马斯克|科技宅变成隔壁老王,马斯克同华裔人妻传绯闻,他的私生活很混乱
- 华裔天才陶哲轩,14岁上大学,31岁获得菲尔兹奖,智商超爱因斯坦
- Intel|Intel重要人事变动 马来华裔半导体大牛陈立武加入董事会
- 什么来头?Meta迎来80后华裔女CFO:15岁考进斯坦福 14年的Meta老兵
- 华人数学家|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揭晓三大奖项
- 夏天宜吃瓜-科技大佬八卦手册:谷歌创始人钟爱华裔女生?
- 这位乌克兰女数学家刚拿到菲尔兹奖,战争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