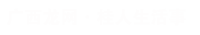王建磊:多方协同参与直播打赏治理,科学界定直播平台责任边界
作者:王建磊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打赏文化自古有之 , 中外皆有 。三国时 , 邯郸淳创作了一篇千字小文《投壶赋》 , 献给魏文帝曹丕 , 曹丕认为写得好 , 遂“赐帛千匹”;西方从18世纪开始盛行的餐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小费”文化 , 不仅成为隐性制度和固定传统 , 还成为体现绅士风度的一种文化自觉及精神需求 。
当网络直播时代开启 , 一群热爱表达、表演的年轻人率先尝鲜 , 他们之中不乏以“才艺、才华、谈吐”见长者 , 且以此征服一众粉丝 , 而粉丝用直播系统中的鲜花、红心、星星等道具(虚拟礼物)来表达对于主播的喜爱与认可 。这些道具真实价格不等 , 都需要真金白银的付出 , “打赏”便成为观看直播的用户购买虚拟礼物赠予主播的自主行为 , 虚拟道具是用户与主播之间进行互动的载体 , 而道具的收益要按照约定比例在主播、公会(有的主播没有参与公会)、平台之间分配 。可以说 , 整个打赏体系的实质是为直播这一新兴媒介所设计的适配盈利模式 , 个体为主播展演内容进行付费的方式直接而高效 , 从而转化为优质内容创作和行业发展的动力 。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 , 将生活场景、个人才艺搬到线上的直播内容 , 不具备传统媒体专业化内容的广告价值 , 而“点对点”的打赏是保证优质内容持续输出和平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之一 。从游戏直播、秀场直播到教育直播再到戏曲直播 , 打赏已经成为用户肯定有用、肯定智慧和肯定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 , 也成为大众广泛接受认可的社会文化 。新媒介形态的直播与打赏文化的相遇 , 可以为繁荣互联网数字经济“添枝加叶” , 然而 , 根据笔者常年爬取的网络直播引起负面报道的数据 , 2016年至今因打赏引起的各类非议、争端、民事、刑事案件等有230余起 , 其中主要有公职人员挪用公款打赏女主播的“违规打赏” , 有未成年人将父母血汗钱付之一炬的“诱导打赏” , 还有一些普通收入者贷款卖房等进行的“过度打赏”等类型 。这些出现在媒体报道视野的非理性案件 , 既把直播行业引入到如洪水猛兽的批判范畴 , 也让公众对于打赏产生误解甚至深恶痛绝之感 。
打赏可看作是用户对于主播付出情感劳动的回报 , 一种良性的促进主播提升内涵和专业技能 , 同时增强用户自身参与感和体验感的方式 。但是部分主播将打赏作为主要的营利手段 , 采用“同质化的网红长相和卖萌献媚”的手段 , 恶意诱导用户打赏 , 这种非理性认知和操作伤害了用户的感情 , 也不利于直播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
迄今 , 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6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11月)、文化部颁布的《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2016年12月)三份文件构建了指引直播行业有规可依、依法发展的法理基础;加上《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2016年4月)、《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规范》《网络直播主播管理规范》(2019年1月)等行业自律条约和地方标准;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18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22年3月)等行政条文 , 可以说 , 围绕直播行业治理的行政法规体系建设已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立体化格局 。在诸多司法实践中 , 一些违规的巨额打赏、行为能力受限者打赏均得到了不同额度退回的支持 。
- 综合目前多方面传闻|iphone14全系钢化膜曝光
- 丁磊|小伙被网贷暴力催收,斗气撸35个平台借17万,现在怎么样了?
- 网络安全|丁磊卸任是为对付马化腾:友谊小船还是说翻就翻了
- |丁磊正在“抛弃”音乐梦
- IT业|丁磊卸任是为对付马化腾:友谊小船还是说翻就翻了
- |51岁卸任CEO,“快乐”丁磊的攻守哲学
- 零售业|丁磊卸任是为对付马化腾:友谊小船还是说翻就翻了
- 腾讯|第9期丨命理中的大佬——网易创始人丁磊
- 丁磊|丁磊也撤了,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风云人物!
- 北斗导航|51岁丁磊卸任:他们都不当CEO了?